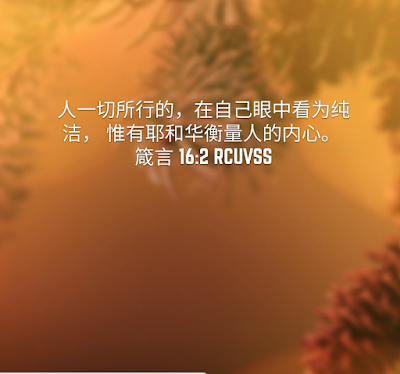一、真理是什麼?
從教父時期到中世紀,神學並沒因著教父豐富的遺產和大公教會深厚的傳統而停滯不前,倒像個不會停止長大的生命一直活躍在人間的舞台,時過境遷,神學仍舊說話。雖來到中世紀,基督教的地位總體蒸蒸日上,但各路登台的神學家卻仍在不懈地努力著如何有效地向當下處境傳講真理,哪怕有時大家對同一事物有著完全相反的認知,比如唯實論和唯名論對共相的理解。
[1] 所以真理就人而言是封閉又開放,是「統一」又「多元」,好比一畫地為牢的界線,是很多不同角度理解不同方面認識的組合,因此真理不是獨裁也不是混亂。在東西方教會為「和子」之爭時,西方的利奧三世雖贊同「和子」的教義,卻始終因著堅守信經不可善作修改的認信,即對大公信仰的忠誠,因此羅馬教會力排眾議拒絕修改信經,
[2] 由此看出中世紀神學圈有一種文化或信念就是重視歷代信徒的共識,哪怕堅持非矛盾原則的大師俄坎也不例外。
[3]
在教父時期,「信而理解」使得真理基本上是釋經的結果,異端如是,所以在真理的獲取上,奧古斯丁的光照論顯得合情合理,因為他們認為除非從上頭來的智慧,不然被罪玷污的罪人是不會靠近真理,更別談認識真理,因此作神學對於教父們來說有個必要的條件就是當事人必須要投入在信仰裡面,簡言之情感要先於理性,所以神學課題很長時間一直圍繞著基督的神人二性,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你我的救恩,因此不管釋經方法強調字意或寓意,真理是來自聖經的。但來到中世紀,隨著神學家們較之前更多更深地接觸和體會聖經之外其他學問的用處,哲學與邏輯在理性的遮蔽下從使女慢慢長成,甚至凌駕於神學,不過這是阿奎那不願意看到的,所以當「理解而信」發展為可能,那麼真理就可以來自理性,簡言之作神學的可以是局外人。
因此在中世紀的神學發展過程中,「上帝存有」的論證成了經院神學避不開的課題,過程中各路豪傑躍躍欲試,都打著自己理解或支持的哲學作為前設,實則視為真理,過程中建造又拆毀,但大致都同意神學因著與哲學的聯姻而受益匪淺,可以先離開啟示(聖經)而單用理性就可以向人言說真理,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存在的、神又何故成為人,因為正如安瑟倫和阿奎那所信:「神哲二學並不矛盾,因為真理同源」,必然理性使得哲學可以證實一切真理,詮釋聖經的教義。
[4] 不過歷史像面鏡子一直在述說一個很似真理的現象即「物極必反」,也就是當人過於強調一個點而失去平衡,一定會遭遇一股強大的反彈,嚴重的會以完全否定的對立而出現。因此到了十四世紀,理性的功能在學術的圈子開始式微,
[5] 而這時神秘主義蒸蒸日上,並以宗教經驗為神學掌舵。
[6] 所以像是蘇格徒或俄坎,他們就重新定義因著認知對象的不同,需要不同的途徑,理性或哲學是局限的,只能從事物存有或過往經驗得以認知,而對超越上帝的認識必須藉著啟示或相信,也就是人無法直接認識上帝,
[7] 即神的物歸神,凱撒的物歸凱撒。但令人詫異的是兩位大家在推翻前人的哲學進路之後,反過來卻仍然沿用另外的哲學進路去論證上帝的存在,蘇格徒推翻阿奎那和奧古斯丁認知方法之後提出從「事物存有」去證明,
[8] 而俄坎認為從「事物被保存」的觀點出發會更具說服力,
[9] 不過他還是認為理性無法證實這位第一保存者就是聖經所講的上帝,也正因此俄坎反過來用邏輯反駁哲學的推論最多只有或然性的功效。
[10]
所以中世紀神學發展到後來,神學與哲學分家,而俄坎似乎完全否定了理性對認識聖經中上帝的功用,
[11] 同時基於他的純一存有和非矛盾原則,俄坎否認人可以認識上帝屬性的「多」,因為在他看來就是「一」,不過他沒否認神是三又一的教義,只把其歸類在奧秘,
[12] 或許奧秘對俄坎來說是非矛盾原則下的無奈。
[13] 但至少三一神向我們揭示在「一」里可以有實際的區別,即三位格,所以真理並非如俄坎所堅持的非矛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可以反合。俄坎把理性在神學教義的認知上拒之門外後,所導致的便是懷疑主義和信心主義。
[14]
那麼真理不是什麼?真理不是主義;那什麼不是真理?哲學的前設不是真理,而看似必然理性的推論也就只能先放置在或然的位置。所以作神學,我們必須不斷地檢視與修正自己的前設,方法只是認識的途徑,方法不是真理,而真理是超越理性邏輯的,我始終相信無論再怎麼篤定基督教的真理,信仰之為信仰,始終離不開是一場冒險,不出意外我宣認的永遠大於我理性所已知的,同時我總是從一個已知跳入另一個未知,未知總是大於已知。再者,我們慣有一種雷同「祂是神,祂就能」的思維,也就是「是真理,就是一」,所以我們作的神學常有主義的氣味,且缺愛與情感,最後只剩下悟性的推理,比如只會指認「他在說褻瀆天父的話」,並謹慎自己「不說褻瀆天父的話」。
不過,「信而理解」的缺點在於易過分運用想像力及邏輯推理,
[15] 發揮已經宣認的教義,或者說在今天強調個體與「眼見為實」的多元處境里,我們有必要先證明前設的可行性,不像中世紀一般上大家會有基本的共識和認同。再則,真理可以被有效地傳遞的確需要我們清晰的表述,學習與掌握技巧是必要的,比如修辭、創意、邏輯學、形上學、哲學等,而這些也能提供我們思辨的方法,充實神學的反省。
[16] 最後,神學的系統化論述需要理性。因此與其說中世紀的神學家在理性上的努力為要闡明基督教信仰是什麼,不如說他們很大程度是為了向尋求理解的人證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從而讓其以情感投入信仰的懷抱。而之後神秘主義的興起也同時讓我們看見真理是需要被實際經歷也是可以被實際經歷的,即心靈需要與神有來往。
二、寓意解經該死?
自初期教會以來,寓意解經一直活躍在釋經工作中,就算到了理性抬頭的中世紀,在尋索上帝的路途上理性仍有其先天的不足,因為上帝有奧秘的一面,因此梅蒙尼德斯認為單靠字面解經是不足夠的,寓意解經有它的功用,這是哲學家必須承認的。
[17] 但現今人看待寓意解經卻常嗤之以鼻,下的斷言一般就是:「天馬行空」,而備受如今教會推崇的當屬字意解經,雖與中古世紀的字意稍有區別,近代人看經文的字意更為豐富除了作者原意之外,還涉及到原初讀者、文學體裁、經文背景等,旨在找出作者原初要傳達的信息,所以秉著找出神要藉著經文在當下傳達怎樣信息的人一律被打入私意解經的大牢。因此我試著指出理性在字意解經上的局限,因為我認為近代人獨尊字意解經法的背後實質是對理性的過於樂觀,認為「字意之法」才是建構靠近經文真意的「真理」,說白了「指月之指」
[18] 成了真理;同時因著神同為聖經的作者,故此藉由中世紀神學家俄坎提出的兩種權能概念,即絕對權能和命定權能,
[19] 來為寓意解經謀取一點公正的對待甚至生存的空間。
詮釋學是否真正存在一套足可應付聖經文本的方法或程序,以致它可以最大化成為衡量別人的詮釋結果?假設存在這樣一種最靠近客觀嚴謹的方法,那是否只要按照這種被普遍認為合法的方法進行釋經,詮釋結果是否都應被尊重?如果存在,似乎假設了這種方法是最安全的。而近來尤其在舊約方面,好像衡量標準是:原始背景、原始讀者和原始作者,也就是作者在什麼背景下,這樣說的目的為何,而原始讀者又是如何理解。如果誰越被人認為靠近以上,似乎誰的解經更具說服力,而在這三個原始元素中似乎是解經者挖掘出來的背景決定了原始讀者聽見什麼和原始作者要說什麼。不過,我們繼續要問的是解經者能獲得這三者的真確能力到底可以有多少?
聖經的特殊性在於它的作者是神和人,而一卷最終形式的正典書卷又可能 經歷過不止一個人的處理。所以“最初”的讀者,到底指哪個作者時代的讀者?因此就不得不決定採用哪個時代的其他文獻來讓你能「真」的看見「聖經」「最原始」的意義,而关键是決定讓誰當「最初」的讀者:是聖經故事裡那個年代中的人?是摩西那個年代的人(先以摩西為五經主體的來源)?還是摩西五經最終正典形式的人?但現實是擺在面前的是最終形式的正典,當我們問這卷書的神學信息或作者写作目的,更常見的是我們常會問上下文為何如此編排。
而一個詞它可以在某個時代有一個意思,但來到後期時,它的意思可能更豐富更飽滿甚至已經超越了原來的所指,也因此「聖經」的「最原始」意義,要以誰為導向?是最終形式正典作者的用意為准?還是其他。所以这「最初」的選擇就顯得要緊和不可或缺,因為只有選對了,才能得以看見「最原始」的意義。而困难在于圣经之外的其他文獻,不是我们可以徹底地、充分地、真确地及完整足夠地掌握。退一步讲,這些文獻也只是代表著那時代一批人的思想,而這批人的代表程度,又或是不是聖經作者所對話的那批人。比如,「保羅新觀」就是根據他們掌握的第二聖殿期文献來解讀保羅的思想,而不贊同的學者在反對的理由中就有一條是指提倡新觀的學者所掌握的文獻不具代表性,指他們只是找了自己要的。可想而知,被原始背景所主导的追求「原始读者」和「原始作者」的诠释方向,是否會把聖經的理解帶向看似嚴謹實質一廂情願的尷尬境地?因為聖經的「最原初」意義是被其他文獻所決定。
而聖經又有一位始終的作者就是上帝,祂一直透過聖經對每個時代的人說話。那麼作者人在他寫下來之後有他局限的理解,和說話的特定群體,但上帝賜下啟示的目的和要對話的群體,卻是超越了作者人和那時代。那麼問題就更复杂了:作者(神和不同人)?讀者(是哪一批?是上帝的讀者?是哪個作者人的讀者)?誰的目的(神學信息),又會不會因著時代不同會有不同方面的强调?因此「最原始」或「最初」,它們的合法性、可知性都是需要被檢討的,因為人理性固有和可達至的視野實在局限又不整全,根本沒法完成樂觀理性所建構的理想。
因此自中古世紀的漫長歷史以來,上帝的命定權能保守了聖經的啟示和教會的詮解,而人要想看見祂的啟示,我相信必須要有聖靈的光照才能聽見聖經的話,那麼我們就需要公正地看待某個時代的某個群體裡特定的寓意解經,他真的是解錯經了嗎,歷世歷代真的都錯了嗎?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上帝的憐憫,好比「解錯經,講對道」,但如果真是這樣到底是我們誤用了聖經還是上帝誤用了權能?單單從聖經的‘字面’‘最原始的意義’‘最初的讀者’去看,固然是大大降低了「私自解經」的成分,但如果聖經是神的話,是神主動藉著人啟示下來,那麼神學信息與要如何發揮它拯救人自然是以神為導向,所以那批得以上帝命定權能保守又有聖靈同在的聖賢在認真寓意解經後真的仍舊屬於解錯經嗎,更何況牧養了整個中古世紀的羊群?
有人說寓意是危險的,或許那些不認真的人會不負責任的天馬行空,但異端往往是源自堅持字面(文學歷史釋經)的堅持:‘以聖經怎麼說我就怎麼理解’的人,所以字意解經常有的試探就是要有深度,就是不一樣的理解,好像前面的聖賢均未能供給他們所需的一樣;
[20]相反寓意解經的不單很難出現異端,還被人指出停滯不前,古舊保守,因為他們是在原有神學框架下指導釋經的,而寓意解經的確更能逼著釋經者思想一個問題:「這段經文對我今天的聽眾要說什麼?」當然有人指責寓意解經被神學所主導,但字意解經者何嘗不是被另外的所左右。比如歷史背景進路的限制在於「基於人們在現代時期實踐這進路時所採納的方法。這進路結合了世界觀、對屬靈現實的懷疑,並對客觀事物的重視,有時會將文本過渡約化。……而且,很多現代的聖經學術研究已發展為十分技術性和專門的學問,參與其中的學者往往會各持己見;在這圈子內,似乎很少事情是確定無疑的。……所以很多曾經有強烈感召進入聖經研究的人,但卻在學習中經驗到現代的聖經學術研究是要他們不再相信聖經。」
[21] 而歷史進路的另一限制,就是只能處理經文在古代處境中的意義,只聚焦於過去的問題,結果令經文受困於過去的歷史。
[22]
美德應是信仰的目的,還是信仰的果子?又或者信仰是美德的結果?不管如何交錯,不可否認,美德自古已經被塞在人的良心裡面,信仰可以不一,但美德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取得了最大的基數。不過基督教的大公信仰卻一再地強調罪才是人類最大最根本的絆腳石,墮落後的人不可能不犯罪也無法自救,凡是對人性抱有樂觀的,都會被趕出大公教會之外,不然被趕出的將會是神完全的恩典,即單就救恩的獲取來說善行和信心常常水火不容,而這也是基督教神學史上一直的迴響。由此觀之,有時站到信仰對立面的可能會是美德,而非罪,
[24] 因為如果罪的反面不是美德卻是信仰的缺乏,那麼在「除罪」上勢必會引發美德與信仰兩者的競爭。而奧古斯丁認為罪是非存有,而惡的出現是因著善的缺乏,
[25] 雖然中世紀的部分神學家重新提出了對罪的定義,比如倫巴都認為罪是人誤用自由意志的結果、亞伯拉德認為在乎人的道德意向,但在上帝之外皆是上帝所造,而所造又都是美善的前提下,大家都同意罪是非存有。不過,從而可知罪有奧秘的一面,是我們理性無法得知的,既然如此我們是沒法用美德(人的善行)去解決人自己罪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去完全掌握罪,以致我們根本沒法篤定自己的方法是可以完全地解決了罪,簡言之在實際的行動中我們常以「罪的反面是美德」來解決罪的問題,尤其在中世紀的懺悔制度顯得尤為明顯,所以面對罪,我們常有的試探是美德(行善積德)。因此我們應該轉向全然知道罪,又全然有能力拯救,又全然有意願拯救的那一位,才會篤定罪會被完全的解決,而那一位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因為終歸而言只有「信仰」才可以解決罪,而非「美德」,因此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雖這並非理性可以證明除了基督教的上帝別無拯救,但卻是在經驗中可以完全經歷理性上的認知,從而繼續從已知跳入未知,不過信仰之為信仰始終是一場冒險,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雖然沒有在理性論證上真正成功過,但他們卻都對當下的尋求理解的人成功證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
四、救恩疑惑
雖然中世紀在人如何得到救恩的事上有很多不一的討論,但大公的信仰都認為人無法靠自己賺取救恩,全然神的恩典在人身上工作的結果;上帝有至高的主權和完全自由的意志,人可以得救完全在於神憑己意主動地揀選;人雖然墮落,但仍然擁有自由意志,人的滅亡完全是自己的責任。所以在以上都成立的前提下,就會出現一直爭論的課題,比如上帝有無預定人滅亡,如果是,那上帝公平嗎?人有自由意志,並且救恩能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完成,無論如何離不開人這個成分,所以比如人的接受算不算一種功用的發揮,雖然連信心也是上帝所賜?因此以下,我從神的恩典是否可被抗拒、接受在救恩上是否有發揮功用的可能、對於滅亡的人上帝是否不公這三方面入手,並且採用中世紀神學家的相關討論去幫助自己理清我該如何回答,儘量避免採用宗教改革後的論述?
1、恩典是否可抗拒?人有沒發揮功用?
神的主權和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恩典是不可抗拒,那麼會危及人的自由意志,也談不上人要為自己的滅亡負責,因為中古神學家同意人的自由意志讓其擔責。如果恩典是可抗拒的,雖保住了人的自由意志,但卻傷害了神的主權,意味上帝原先的揀選失敗了。當然中世紀的神學家有不少的想法,比如從預定和預知入手。我的想法如下,但藉用中世紀的思維作為我以下討論的前提:上帝是偉大的真神,對於萬物來說,當他真看見了這位偉大的上帝,就一定會被吸引。
救恩的恩典可抗拒还是不可抗拒,會不會是问错了问题,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把神賜給人信心,然後這個人信了主的過程,好比神向他顯現,他也看見了偉大又真的神,那麼當他看見後一定會有的行為就是在自由意志里歡喜快樂如獲至寶的投奔向真神,不存在掙扎或任何思考的「選擇」,也就是不會出現「選擇」,若是這樣「接受」其实不适合用来描述人對救恩的回應,反而有误导的可能。
其實恩典形容神為我們所作一切的性質,所以從這個角度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因為我們沒法料想更談不上阻止神在祂完全的自由意志里向我們顯現,因此如果救恩恩典的內容是神的顯現,那麼就是不可抗拒的,至於人看見顯現後如何回應救恩,如上所言(也是論述的前設)。所以任何途徑都可以成為上帝顯現的管道(途徑),最常見的就是宣教傳福音。因此再舉個例子:事先我承諾接下來如果他們想要哪個包裹,那裡面有的也一併送給他,因此兩包包裝一模一樣的,其中一個有書另外是空的,接著讓每人摸一下,摸完之後,大家都會知道有書的包裹,而假設大家知道後一定會想要這個裝著書的包裹,所以他們肯定會變成想要並希望我能兌現之前的諾言(諾言好比宣講的福音),而不是說他接受包裹,同時不存在抗拒和不可抗拒的問題。
2、對於滅亡的人,上帝公平吗?
人一談到公平是從受益者的一方去發問的,受益者基於自己的某種努力滿足了一定標準及某種意義上一樣的規則,被承諾一定會被給予或者得到或者賺取某樣東西。
但救恩不是在於人的行為,是上帝的東西又是基於祂自己的意願白白地賜給某些人,也就是說上帝有權利如何對待祂的東西。舉例:兩個男生公平競爭,也就是不走歪門邪道、光明正大,過程都盡力了,結果女生選擇了其中一個男生,而另外一個男生是不會說這個女生的選擇不公平,因為知道這是她的權利,所以也應該尊重她的選擇。如果非要女生說選擇他也必須選擇我,那對這女孩子是不公平的,因為你沒有權利做出這樣的要求並這要求是蠻橫無理的,自我又粗暴。不過,除非女孩子事先承諾過,要按著雙方表現的行為,如果誰達至了這樣可以量化的標準,那我就選擇他,這時同樣達至標準而落選的男生大可以指責這位女生不公平。所以,那男生不應該有太多哀怨,因為盡力了,也會羨慕那被選上的真幸運。
但真如上例所言,一進入救恩的情境,似乎還是不能責怪落選的人,因為人沒能力攔阻祂的權利或強迫祂實行我的要求,所以部分人滅亡的原因應歸責給神沒有揀選拯救的緣故,是這樣嗎?決然不是。因為人的起點也就是水平線,原本就是有罪因罪要死,而不是「被拯救活—沒被拯救死」的法則導致了「死」。所以根本原因不是上帝沒有實行拯救而致人死亡,死是因為自己的罪。如果我們採納中世紀神學家的看法:如果沒有罪就不會死也就不用被拯救,那麼按「受益者的公平法則」,論罪處斬也就是按行為受罰是公平的,不按著行為而被拯救的反而是被不公平了。就好像你為什麼還是單身,不是那女生沒有選擇你,而是你本來就是單身。所以是我們本來就要死,按著公義的審判,也就是你我的行為:罪行。原來反而是拯救沒有照著人的行為,審判卻按著人的行為。
雖然不管「是否預定人不被拯救」,但不可否認神揀選的側面一定同時有審判的成分。我們常說「對於滅亡的人,上帝公平嗎?」,或許我們該換過來問「對於擁有本相權利的上帝,本該滅亡人的無理要求公平嗎?」,如果你真的這麼在乎公平。
[1] 林榮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二):中世紀教會》(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428-29。
[18] 馬可士·伯格,《重閱聖經:重新進入文本世界,發掘聖經的深邃真意》(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44。
[19] 同上,435。絕對權能:上帝可藉著絕對權能,作任何本身沒有矛盾的事;命定權能:上帝在祂所建立的秩序中實際去作或已作成的。也就是說兩種權能涉及不同的範疇:命定權能處理上帝決定作的;而絕對權能事關乎上帝能夠作的。前者是針對世界的管制、永恆的計劃,透過聖經的啟示和教會的詮釋,上帝的定旨是人可明白的。而後者乃超越時空,不為世人所知,是上帝的自由意志,並且絕對權能是凌駕於命定權能之上,甚至取締它。上帝的行動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左右,也不受先前所定規的程序限制。
[20] 林榮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二)》,221。
[21] 馬可士·伯格,《重閱聖經》,49-50。
[23] 美德對應的就是善行,而信仰是指信心或神完全的恩典,是信而仰的一種姿態。
[24] 某些否定的人會說還是罪,因為「罪影響人對真理的認識」,我暫且把這個說法放在一邊,以免走入都以「罪」一言蔽之的死循環。
[25] 林榮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二)》,216。